时钟的数字在挣扎,跳动,跳动,每一次回弹都像钝刀割在喉咙上,距离终场蜂鸣器发出那声终结或解放的嘶吼,还剩7分12秒,比分牌上,那微不足道的3分领先优势,在万人嘶吼的声浪里,薄得像一张随时会被扯碎的纸,整座球馆,从地板缝到穹顶的每一盏射灯,都浸泡在一种濒临沸点的、金黄色的躁郁里,空气浓稠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与汗水的灼热,对手的眼神里,是困兽被逼到悬崖边,闪着幽幽绿光的决绝。
他接球了。

多诺万·米切尔,在弧顶,左手随意地搭着那颗橘红色的斯伯丁,世界在他接球的一刹那,仿佛被按下了某种诡异的降噪键,四周奔袭的对手、挥舞的手臂、看台上翻涌的人浪、甚至是队友急切要位的呼喊,都急速褪去,模糊成一片嗡嗡的背景杂音,聚光灯下,只有他,和篮筐之间,那条由九双不停交错移动的腿所把守的、荆棘丛生的路径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站在这里,盐湖城冰冷高原上那些被质疑包裹的夜晚,克利夫兰重建初期独自扛起球队蹒跚前行的黄昏,无数个在训练馆里与自己的心跳和运球声为伴的凌晨,所有的记忆碎片,此刻都沉淀为他瞳孔里那两汪深不见底的漆黑潭水,压力?不,那太奢侈了,对于一只自幼就懂得在街头用篮球对抗整个街区喧嚣的“蜘蛛”这满场的敌意,不过是又一片需要他亲手编织秩序的丛林。
他开始运球,左手,右手,再拉回左手,球撞击地板的“砰、砰”声,并不迅疾,却奇异地压过了所有噪音,成为此刻球馆唯一的心跳,那不是一个攻击的前奏,更像是一场独奏会的第一个和弦,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,他在丈量,用每一次胯下换手、每一次犹豫步的悬浮,丈量着防守者呼吸的间隙、重心偏移的毫厘,以及整条防线随着他这“人类节拍器”的韵律而产生的、肉眼难辨的集体脉动。
对手的王牌防守者贴了上来,肌肉贲张,像一堵移动的墙,米切尔肩部向左一个迅猛的抖动,防守者的髋部立刻做出反应,但就在电光石火间,那向左的力量被硬生生收回,仿佛从未发生,真正的杀招是向右那一步沉静却致命的跨出——不是绝对的速度,而是变速,是让防守者引以为傲的反应系统,在他精心编织的“停顿—加速—再停顿”的节奏陷阱里彻底死机,一个身位的空档,就此撕开,那不是速度的胜利,那是时序的谋杀。
他深入腹地,像一柄精确的手术刀划开黄油,内线的补防巨塔已然升起,遮天蔽日,时间的选择在此刻达到艺术的峰值:早零点一秒,会被封盖;晚零点一秒,协防将至,就在那巨掌即将笼罩皮球的瞬间,米切尔在空中完成了一次违背物理学的蜷缩、展腹,指尖将球轻柔地擦向篮板一个不可思议的高点,球在篮筐上沿亲吻了一下,顺从地滚入网窝,不是暴扣,却比任何暴扣都更能摧毁对手的意志——它宣告着,在这方天地间,重力、角度、封盖,一切物理规则与防守努力,都臣服于他此刻所设定的节奏之下。

这就是“完全掌控”,它远不止是得到30分或40分,那只是冰冷的数据,它是让一场决定生死的、充斥着野兽般身体对抗的西决之战,在最后半节里,神奇地进入了“米切尔时间”,他的每次处理球——无论是一次压到24秒将至的冷静分球,找到底角被放空的射手;还是一次造成犯规后,在声浪顶峰中稳稳命中的两次罚球——都在将比赛切割成他所熟悉的、一段一段的段落,对手的追分狂潮,像猛浪撞上岿然的礁石,不是被击碎,而是被他的节奏吸吮、消化,最终成为他演奏乐章里一段被驯服的、渐弱的插曲。
当终场哨响,记分牌定格,整个系列赛的命运就此转向,米切尔平静地走向场地中央,汗水浸透的战袍紧贴着他起伏的胸膛,没有歇斯底里的咆哮,没有夸张的庆祝,只有一种深沉的、接近疲惫的平静,他抬头望向漫天飞舞的彩带,眼神穿过狂欢的人群,仿佛在确认着什么。
他确认了,今夜,在这片足以吞噬所有巨星的、名为“西决生死战”的沸腾海洋里,他不是随波逐流的舟,而是那个定义海流方向的人,他驯服的不仅仅是对手的防守,更是这令人窒息的夜晚本身,把一场集体性的疯狂,变成了他个人意志的绝对证明,篮球在他手中,从来就不仅是得分的工具,而是掌控时间的权杖,当世界喧嚣,他便成为寂静的中心;当万物狂奔,他便定义何为静止,这,便是节奏的暴君,于无声处,听惊雷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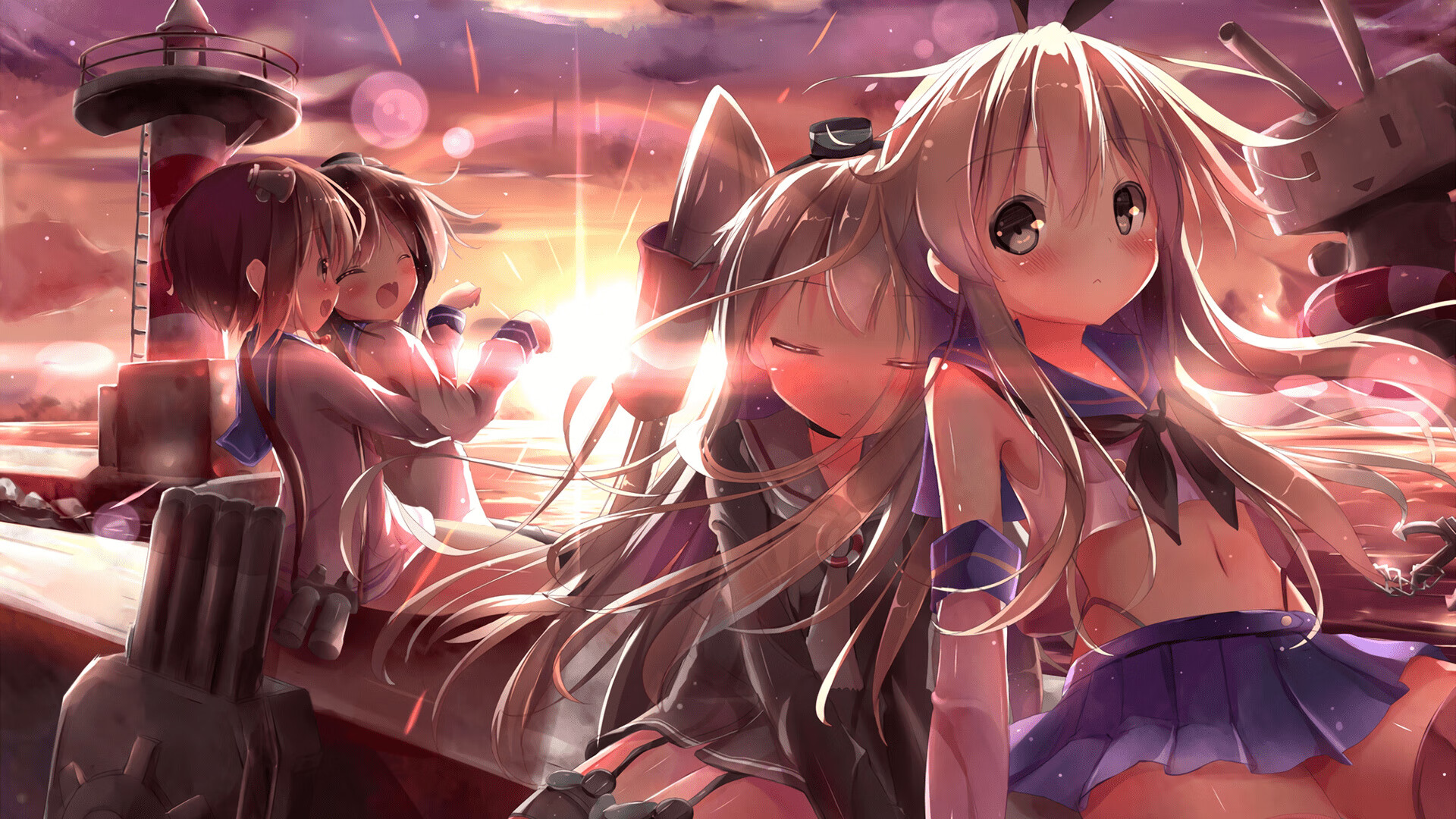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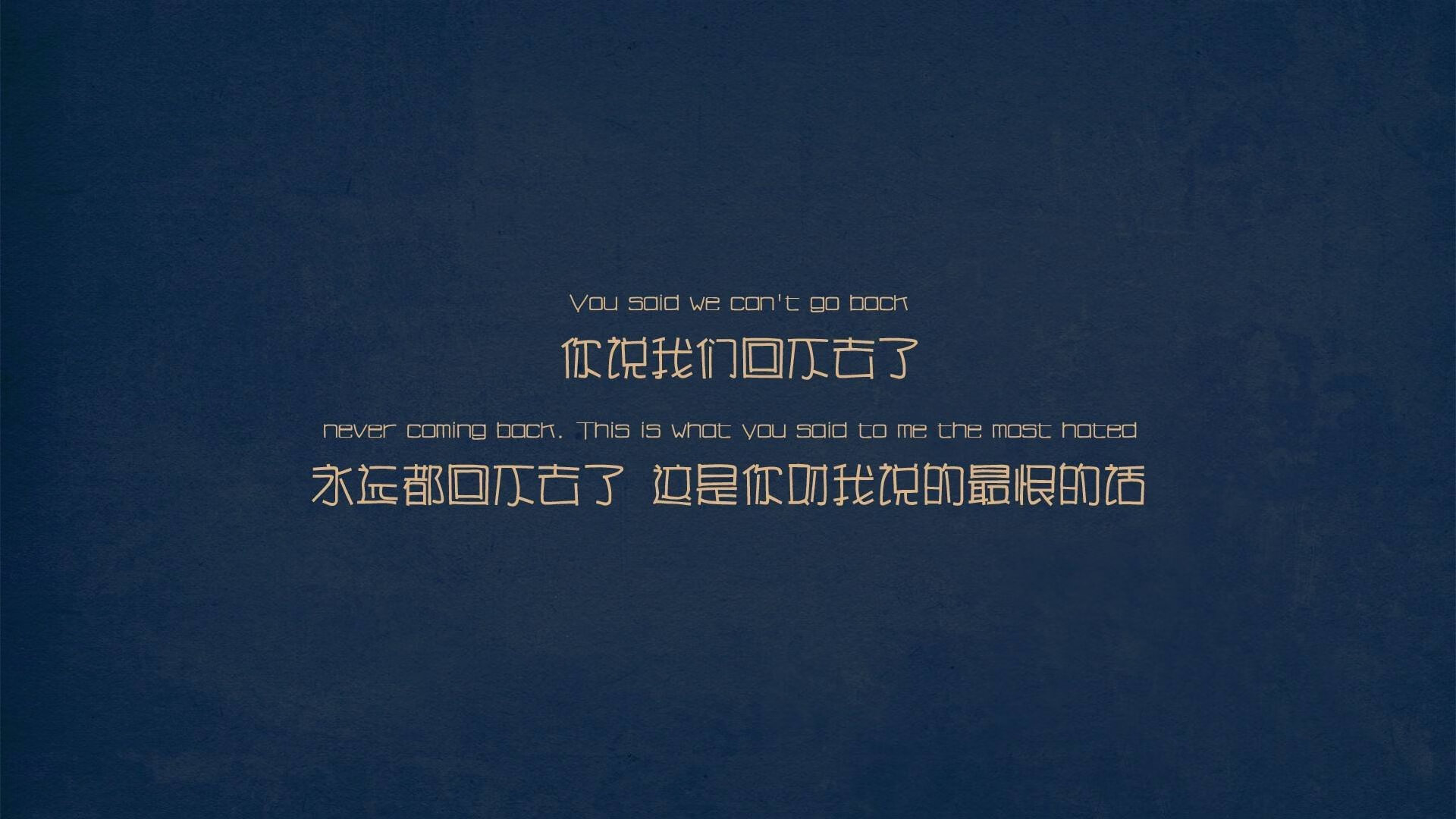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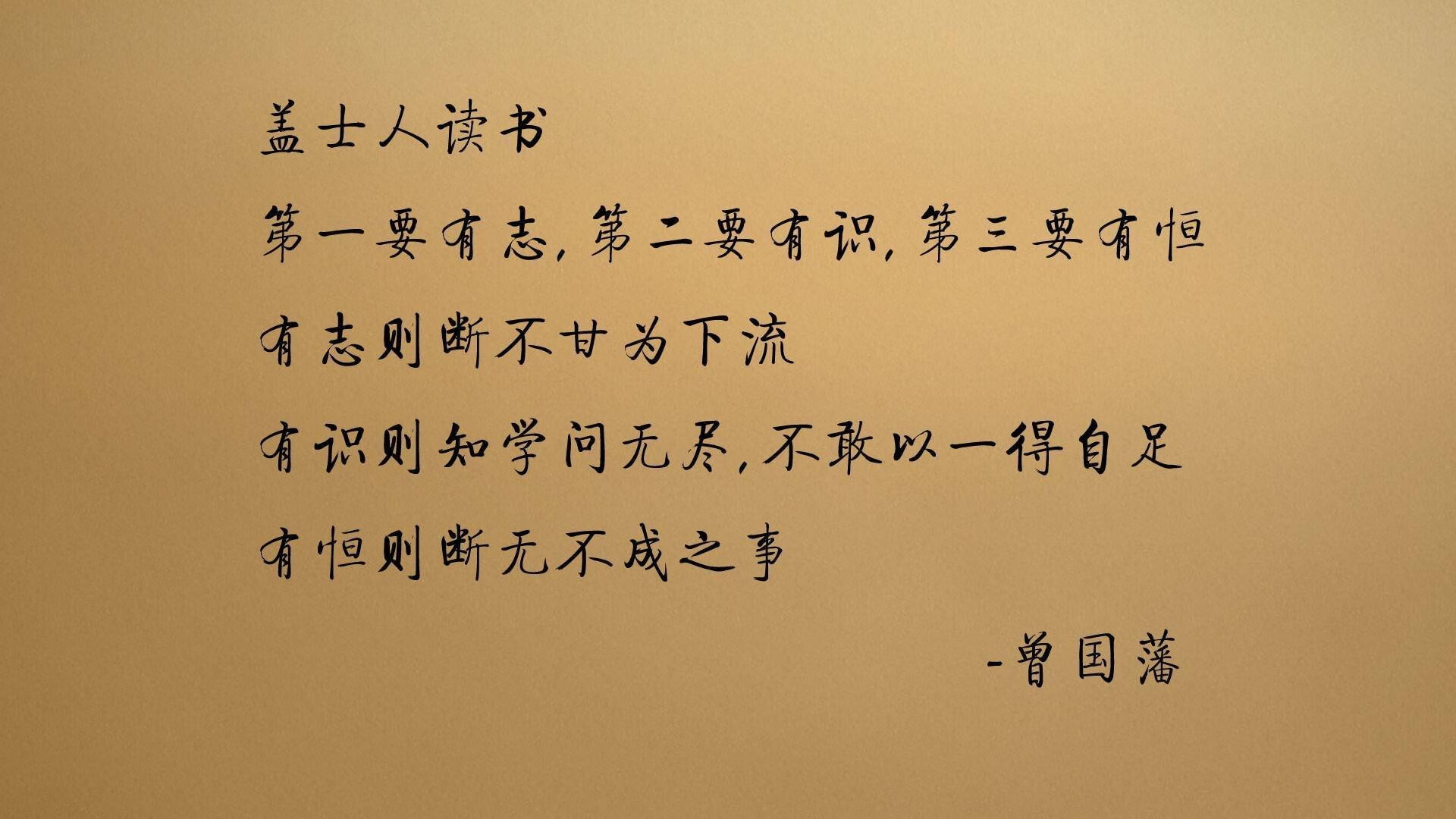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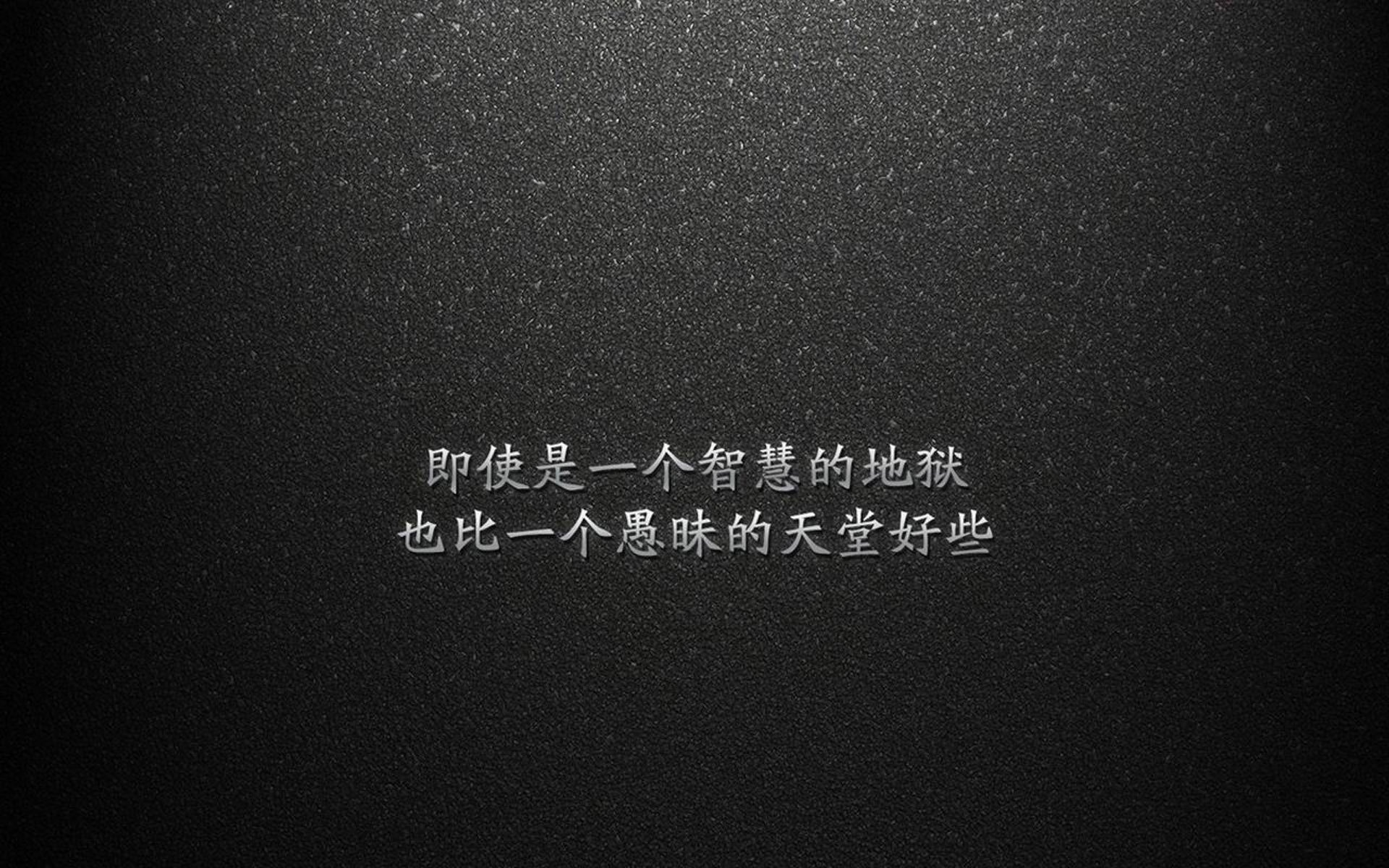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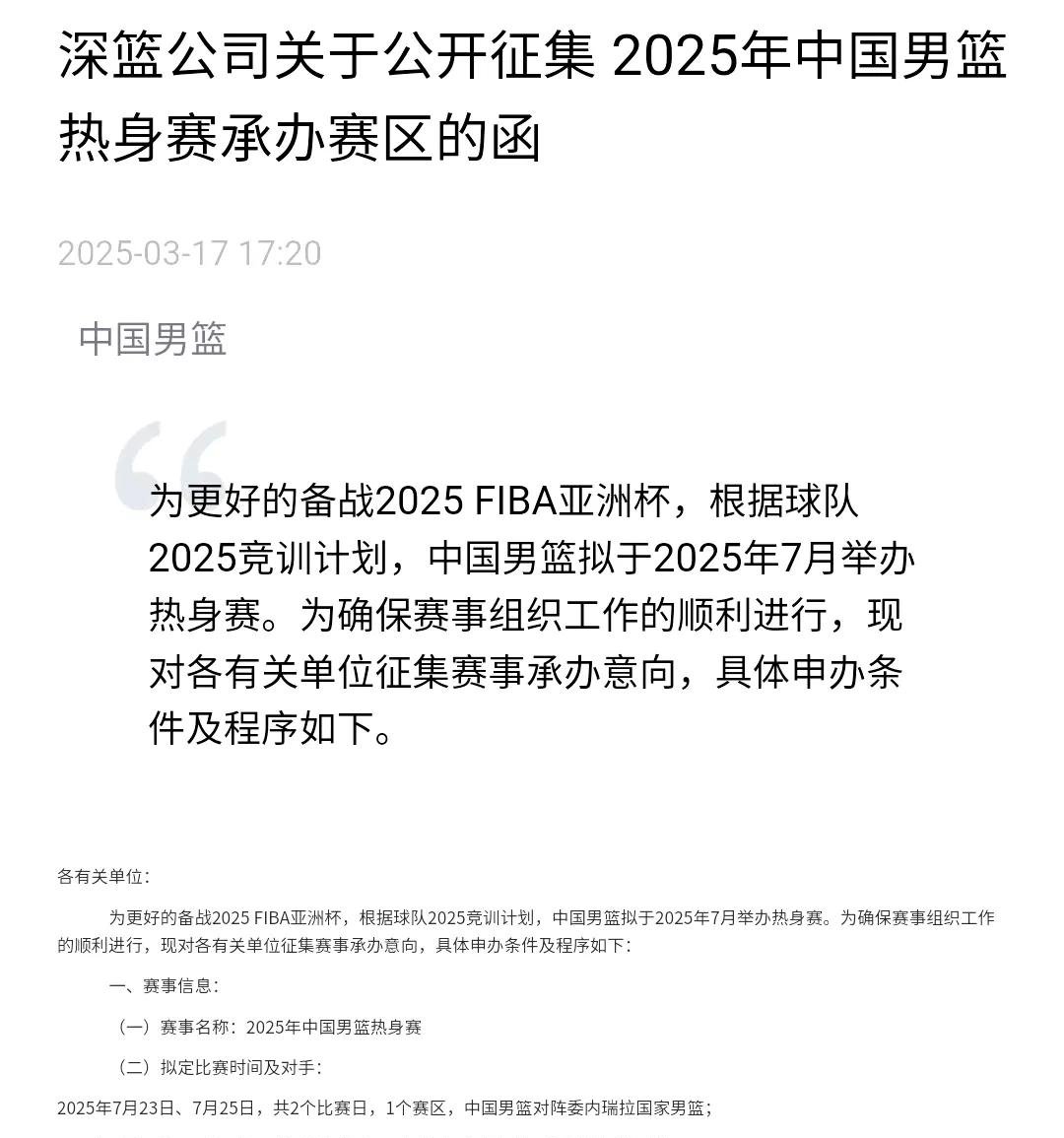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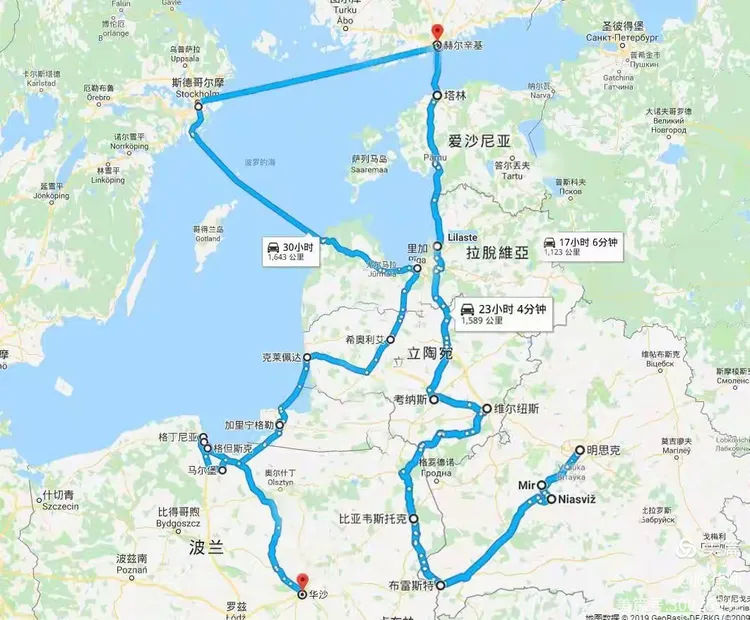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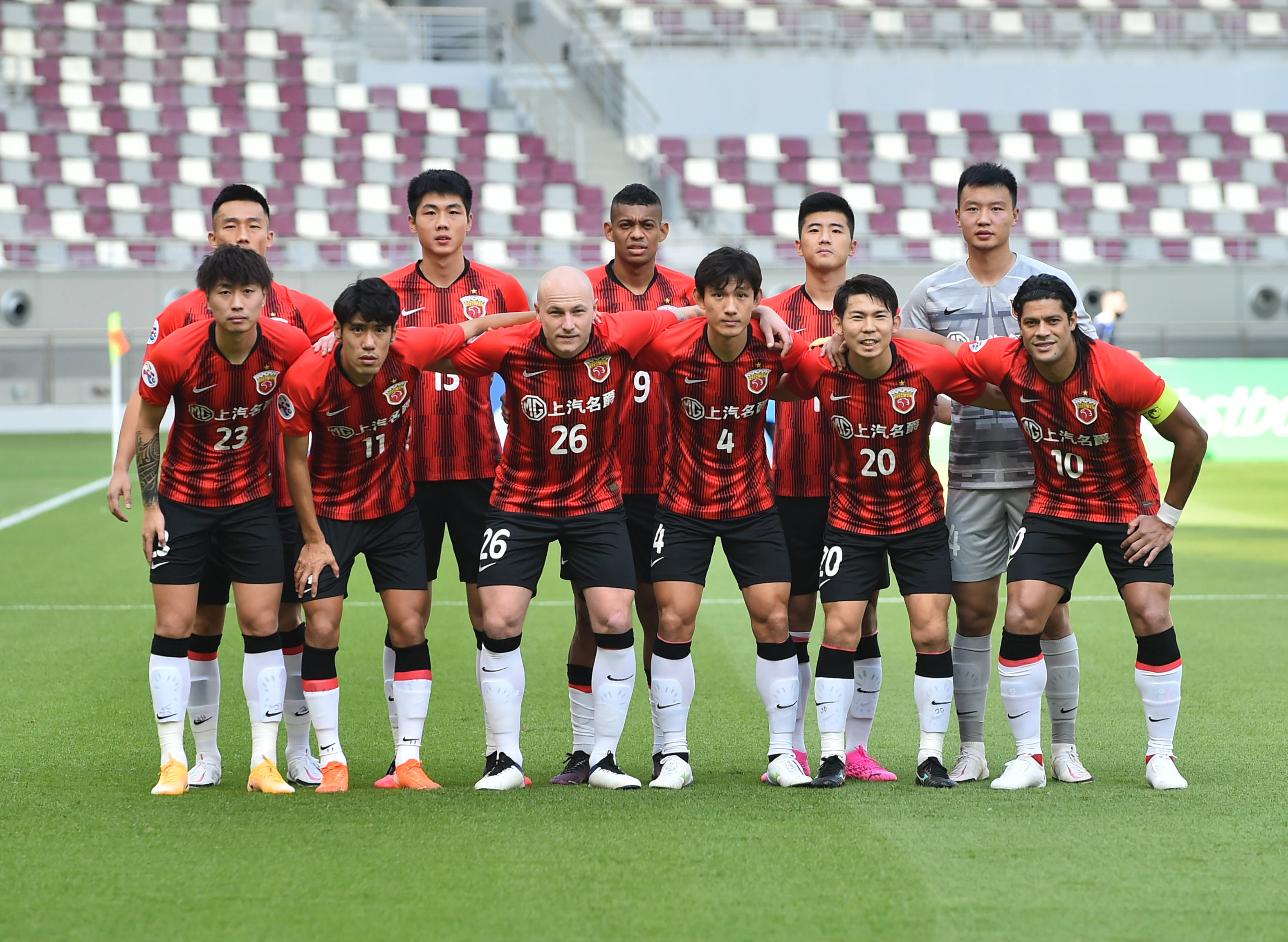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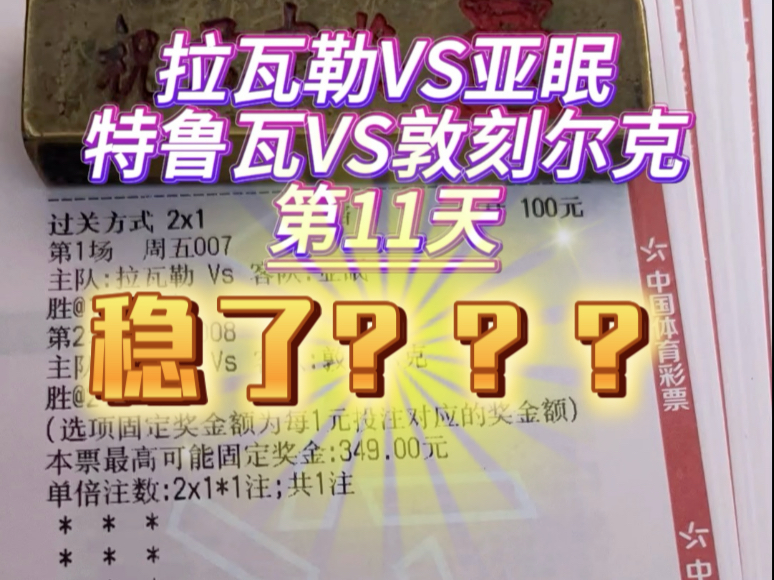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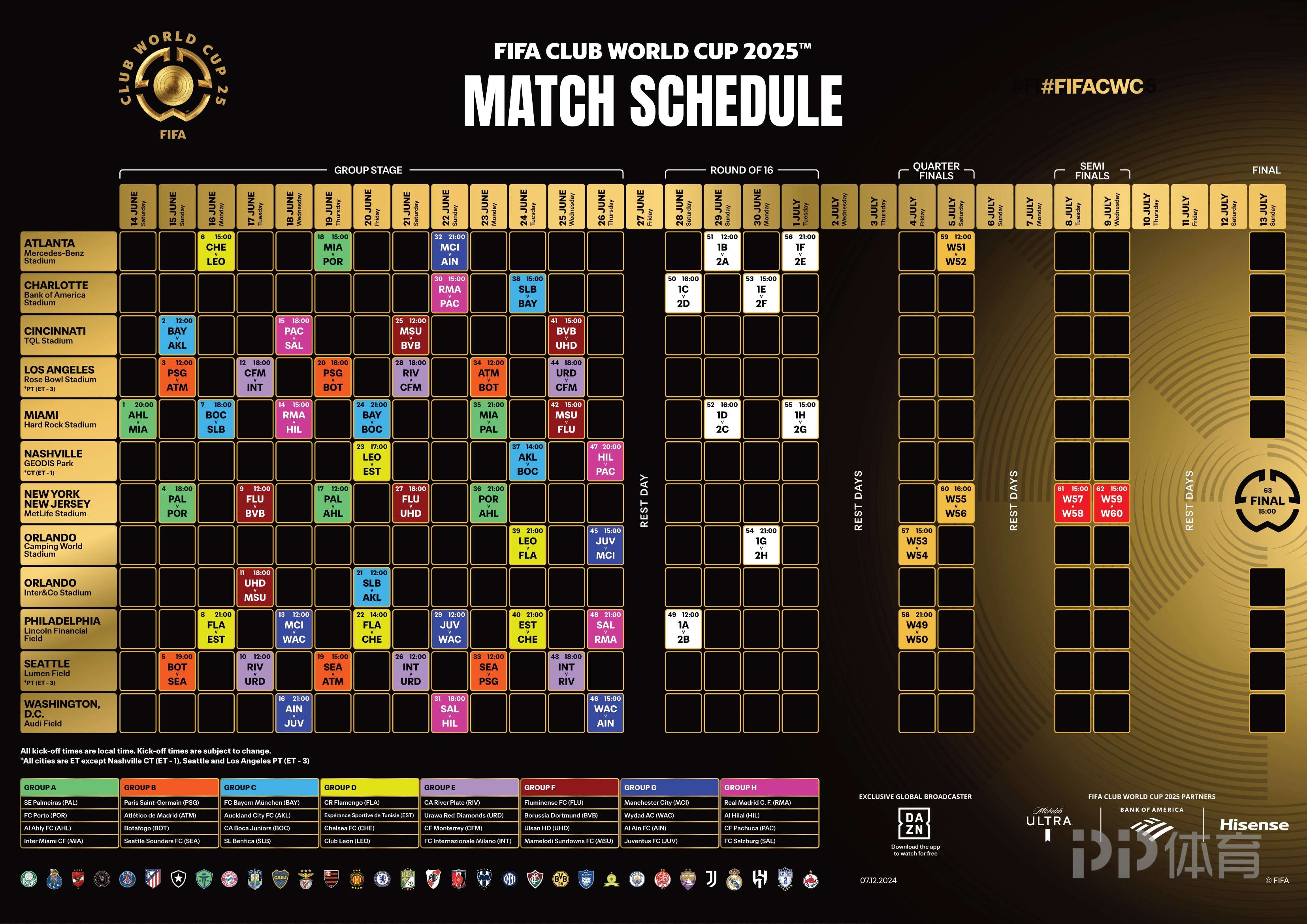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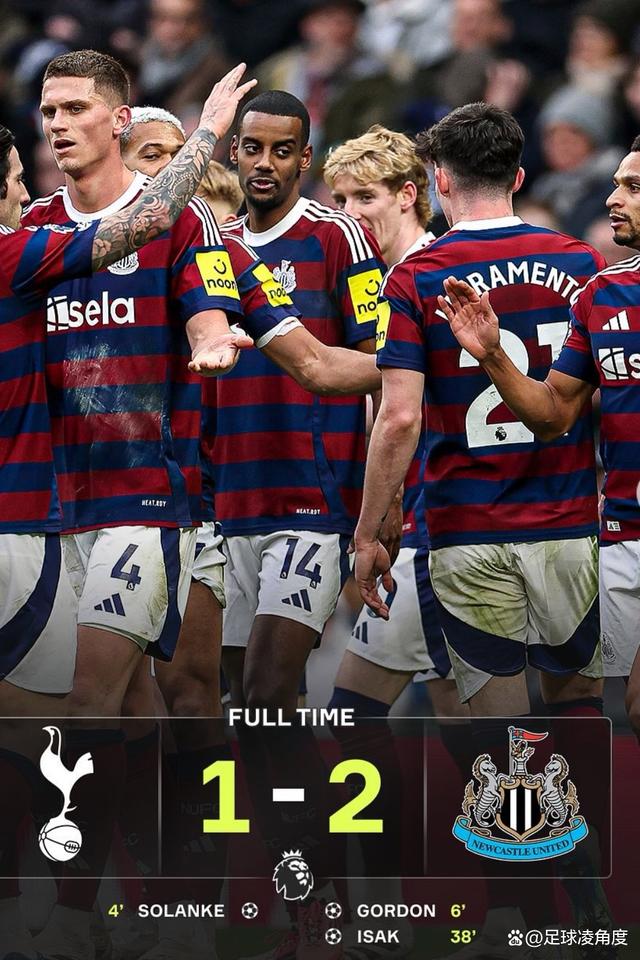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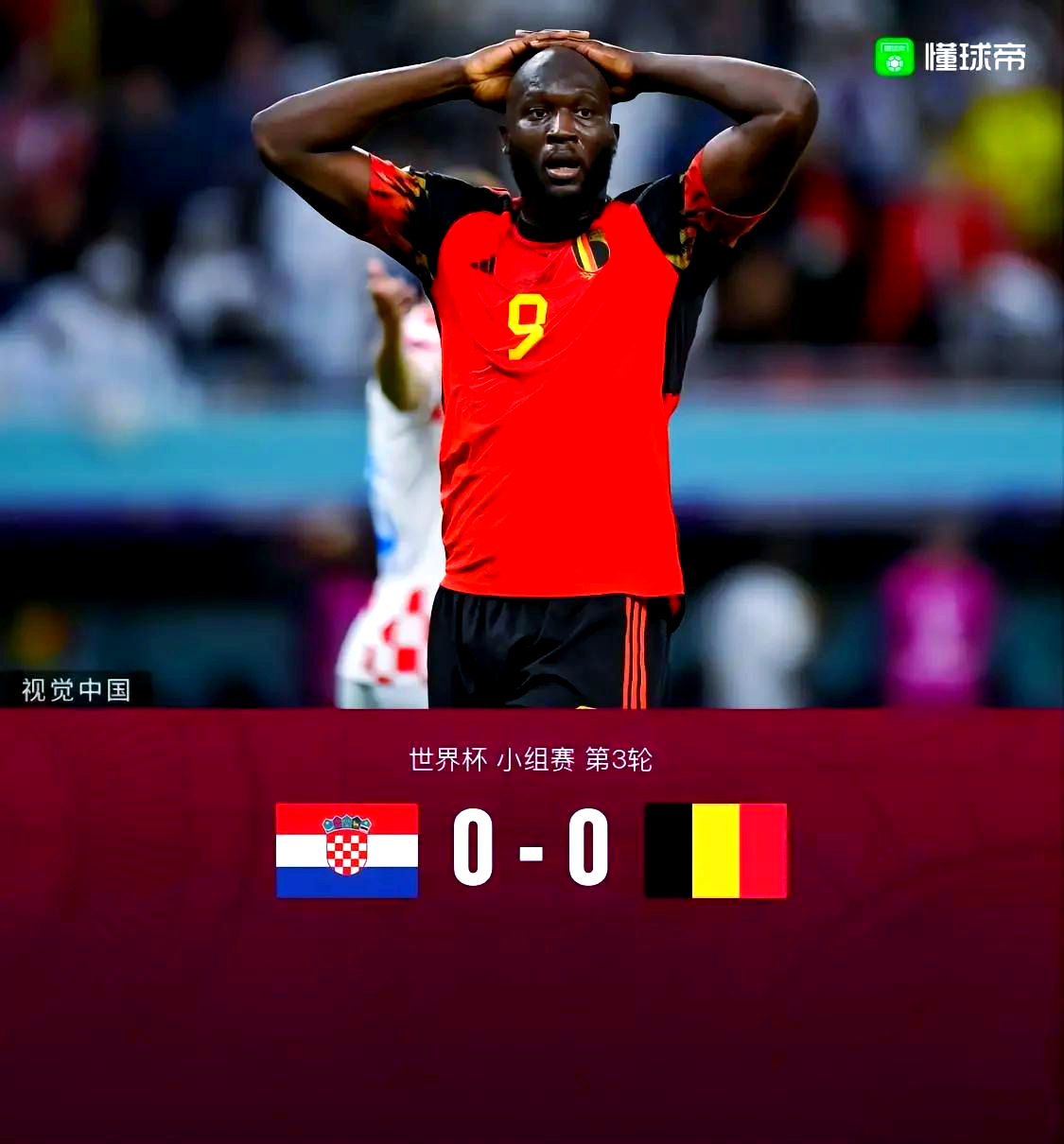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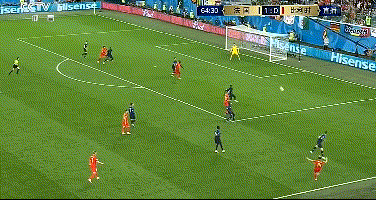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网友评论
最新评论